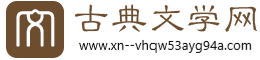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
话说当时武松踏住蒋门神在地下,道:“若要我饶你性命,只依我三件事,便罢!”蒋门神便道:“好汉但说。蒋忠都依。”武松道:“第一件,要你便离了快活林,将一应家火什物随即交还原主金眼彪施恩。谁教你强夺他的?”蒋门神慌忙应道:“依得!依得!”武松道:“第二件,我如今饶了你起来,你便去央请快活林为头为脑的英雄豪杰都来与施恩陪话。”蒋门神道:“小人也依得!”武松道:“第三件,你从今日交割还了,便要你离了这快活林,连夜回乡去,不许你在孟州住;在这里不回去时,我见一遍打你一遍,我见十遍打十遍!轻则打你半死,重则结果了你命!你依得麽?”蒋门神听了,要挣扎性命,连声应道:“依得!依得!蒋忠都依!”
武松就地下提起蒋门神来看时,早已脸青嘴肿,脖子歪在半边,额角头流出鲜血来。武松指着蒋门神,说道:“休言你这厮鸟蠢汉!景阳冈上那只大虫,也只三拳两脚,我兀自打死了!量你这个直得甚的!快交割还他!但迟了些个,再是一顿,便一发结果了你这厮!”
蒋门神此时方才知是武松,只得喏喏连声告饶。正说之间,只见施恩早到,带领着三二十个悍勇军健,都来相帮;却见武松赢了蒋门神,不胜之喜,团团拥定武松。武松指着蒋门神,道:“本主已自在这里了,你一面便搬,一面快去请人来陪话!”蒋门神答道:“好汉,且请去店里坐地。”
武松带一行人都到店里看时,满地都是酒浆,入脚不得;那两个鸟男女正在缸里扶墙摸壁挣扎;那妇人方才从缸里爬得出来,头脸都吃磕破了,下半截淋淋漓漓都拖着酒浆;那几个火家酒保走得不见影了!
武松与众人入到店里坐下,喝道:“你等快收拾起身!”一面安排车子,收拾行李,先送那妇人去了;一面寻不着伤的酒保,去镇上请十数个为头的豪杰,都来店里替蒋门神与施恩陪话。尽把好酒开了,有的是按酒,都摆列了面,请众人坐地。武松叫施恩在蒋门神上首坐定。各人面前放只大碗,叫把酒只顾筛来。
酒至数碗,武松开话道:“众位高邻都在这里:我武松自从阳谷县杀了人配在这里,便听得人说道:‘快活林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营造的屋宇等项买卖,被这蒋门神倚势豪强,公然夺了,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饭。’你众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,我和他并无干涉。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!我若路见不平,真乃拔刀相助,我便死也不怕!今日我本待把蒋家这厮一顿拳脚打死,就除了一害;我看你众高邻面上,权寄下这厮一条性命。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。若不离了此间,我再撞见时,景阳冈上大虫便是模样!”
众人才知道他是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,都起身替蒋门神陪话,道:“好汉息怒。教他便搬了去,奉还本主。”
那蒋门神吃他一吓,那里敢再做声。施恩便点了家火什物,交割了店肆。蒋门神羞惭满面,相谢了众人,自唤了一辆车儿,就装了行李,起身去了,不在话下。
且说武松邀众高邻直吃得尽醉方休。至晚,众人散了,武松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。
却说施老管营听得儿子施恩重霸快活林酒店,自骑了马直来酒店里相谢武松,连日在店内饮酒作贺。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,那一个不来拜见武松。自此,重整店面,开张酒肆。老管营自回平安寨理事。
施恩使人打听蒋门神带了老小不知去向,这里只顾自做买卖,且不去理他,就留武松在店里居住。自此,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,各店里并各睹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。施恩得武松争了这口气,把武松似爷娘一般敬重。施恩自从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,不在话下。
荏苒光阴,早过了一月之上。炎威渐退,玉露生凉;金风去暑,已及新秋。有话即长,无话即短。当日施恩在和武松在店里闲坐说话,论些拳棒枪法。只见店门前,两三个军汉,牵着一匹马,来店里寻问主人,道:“那个是打虎的武都头?”
施恩却认得是孟州守御兵马都监张蒙方衙内亲随人。施恩便向前问道:“你们寻武都头则甚?”那军汉说道:“奉都监相公钧旨,闻知武都头是个好男子,特地差我们将马来取他。相公有钧贴在此。”
施恩看了,寻思道:“这张都监是我父亲的上司官,属他调遣。今者,武松又是配来的囚徒,亦属他管下,只得教他去。”施恩便对武松道:“兄长,这几位郎中是张都监相公处差来取你。他既着人牵马来,哥哥心下如何?”
武松是个刚直的人,不知委曲,便道:“他既是取我,只得走一遭,看他有甚
话说。”随即换了衣裳巾帻,带了个小伴当,上了马,一同众人投孟州城里来。到得张都监宅前,下了马,跟着那军汉直到厅前参见张都监。那张蒙方在厅上,见了武松来,大喜道:“教进前来相见。”
武松到厅下,拜了张都监,叉手立在侧边。张都监便对武松道:“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,男子汉,英雄无敌,敢与人同死同生。我帐前现缺恁地一个人,不知你肯与我做亲随梯已人麽?”武松跪下,称谢道:“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;若蒙恩相抬举,小人当以执鞭随镫,服侍恩相。”
张都监大喜,便叫取果盒酒出来。张都监亲自赐了酒,叫武松吃得大醉,就前厅廊下收拾一间耳房与武松安歇。次日,又差人去施恩处取了行李来,只在张都监家宿歇。早晚都监相公不住地唤武松进后堂与酒与食,放他穿房入户,把做亲人一般看待;又叫裁缝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。武松见了,也自欢喜,心里寻思道:“难得这个都监相公一力要抬举我!自从到这里住了,寸步不离,又没工夫去快活林与施恩说话。……虽是他频频使人来相看我,多管是不能够入宅里来?……”
武松自从在张都监宅里,相公见爱,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,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,无有不依。外人俱送些金银、财帛、段匹……等件。武松买个柳藤箱子,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,不在话下。
时光迅速,却早又是八月中秋。张都监向后堂深处鸳鸯楼下安排筵宴,庆赏中秋,叫唤武松到里面饮酒,武松见夫人宅眷都在席上,吃了一杯便待转身出来。张都监唤住武松,问道:“你那里去?”武松答道:“恩相在上:夫人宅眷在此饮宴,小人理合回避。”张都监大笑道:“差了;我敬你是个义士,特地请将你来一处饮酒,如自家一般,何故却要回避?”便教坐了。武松道:“小人是个囚徒,如何敢与恩相坐地。”张都监道:“义士,你如何见外?此间又无外人,便坐不妨。”
武松三回五次谦让告辞。张都监那里肯放,定要武松一处坐地。武松只得唱个无礼喏,远远地斜着身坐下。张都监着丫环养娘相劝,一杯两盏。
看看饮过五七杯酒,张都监叫抬上果桌饮酒,又进了一两套食;次说些闲话,问了些枪法。张都监道:“大丈夫饮酒,何用小杯!”叫:“取大银赏锺斟酒与义士吃。”连珠箭劝了武松几锺。
看看月明光彩照入东窗。武松吃得半醉,却都忘了礼数,只顾痛饮。张都监叫唤一个心爱的养娘,叫做玉兰,出来唱曲。张都监指着玉兰道:“这里别无外人,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头在此。你可唱个中秋对月时景的曲儿,教我们听则个。”玉兰执着象板,向前各道个万福,顿开喉咙,唱一只东坡学士“中秋水调歌”。唱道是:
明月几时有!把酒问青天: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?我欲乘风归去,只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?卷珠帘,低绮户,照无眠,不应有恨,何事常向别时圆?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!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!
这玉兰唱罢,放下象板,又各道了一个万福,立在一边。张都监又道:“玉兰,你可把一巡酒。”这玉兰应了,便拿了一副劝盘,丫环斟酒,先递了相公,次劝了夫人,第三个便劝武松饮酒。张都监叫斟满着。武松那里敢抬头,起身远远地接过酒来,唱了相公夫人两个大喏,拿起酒来一饮而尽,便还了盏子。
张都监指着玉兰对武松道:“此女颇有些聪明,不惟善知音律,亦且极能针指。如你不嫌低微,数日之间,择了良时,将来与你做个妻室。”武松起身再拜,道:“量小人何者之人,怎敢望恩相宅眷为妻。枉自折武松的草料!”张都监笑道:“我既出了此言,必要与你。你休推故阻我,必不负约。”当时一连又饮了十数杯酒。约莫酒涌上来,恐怕失了礼节,便起身拜谢了相公夫人,出到前厅廊下房门前,开了门,觉道酒食在腹,未能便睡,去房里脱了衣裳,除了巾帻,拿条哨棒来,庭心里,月明下,使几回棒,打了几个轮头;仰面看天时,约莫三更时分。
武松进到房里,却待脱衣去睡,只听得后堂里一片声叫起有贼来。武松听得道:“都监相公如此爱我,他后堂内里有贼,我如何不去救护?”武松献勤,提了一条哨棒,迳抢入后堂里来。只见那个唱的玉兰慌慌张张走出来指道:“一个贼奔入后花园里去了!”
武松听得这话,提着哨棒,大踏步,直赶入花园里去寻时,一周遭不见;复翻身却奔出来,不提防黑影里撇出一条板凳,把武松一交绊翻,走出七八个军汉,叫一声“捉贼”,就地下,把武松一条麻索绑了。武松急叫道:“是我!”那众军汉那里容他分说。只见堂里灯烛荧煌,张都监坐在厅上,一片声叫道:“拿将来!”
众军汉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厅前,武松叫道:“我不是贼,是武松!”张都监看了大怒,变了面皮,喝骂道:“你这个贼配军,本是贼眉贼眼贼心贼肝的人!我倒抬举你一力成人,不曾亏负了你半点儿!却才教你一处吃酒,同席坐地,我指望要抬举与你个官,你如何却做这等的勾当?”武松大叫道:“相公,非干我事!我来捉贼,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贼?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,不做这般的事!”张都监喝道:“你这厮休赖!且把他押去他房里,搜看有无赃物!”
众军汉把武松押着,迳到他房里,打开他那柳藤箱子看时,上面都是些衣服,下面却是些银酒器皿,约有一二百两赃物。武松见了,也自目瞪口呆,只叫得屈。众军汉把箱子抬出厅前,张都监看了,大骂道:“贼配军!如此无礼!赃物正在你箱子里搜出来,如何赖得过!常言道:‘众生好度人难度!’原来你这厮外貌像人,倒有这等禽心兽肝!既然赃证明白,没
话说了!”——连夜便把赃物封了,且叫送去机密房里监收。——“天明却和这厮说话!”
武松大叫冤屈,那里肯容他分说。众军汉扛了赃物,将武松送到机密房里收管了。张都监连夜使人去对知府说了,押司孔目,上下都使用了钱。
次日天明,知府方才坐厅,左右缉捕观察把武松押至当厅,赃物都扛在厅上。张都监家心腹人赍着张都监被盗的文书呈上知府看了。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。牢子节级将一束问事狱具放在面前。武松却待开口分说,知府喝道:“这厮原是远流配军,如何不做贼!一定是一时见财起意!既是赃证明白,休听这厮胡说,只顾与我加力打!”那牢子狱卒拿起批头竹片,雨点的打下来。
武松情知不是话头,只得屈招做“本月十五日一时见本官衙内许多银酒器皿,因而起意,至夜乘势窃取入己。”与了招状。知府道:“这厮正是见财起意,不必说了!且取枷来钉了监下!”牢子将过长枷,把武松枷了,押下死囚牢里监禁了。
武松下到大牢里,寻思道:“叵耐张都监那厮安排这般圈套坑陷我!我若能够挣得性命出去时,却又理会!”牢子狱卒把武松押在大牢里,将他一双脚昼夜匣着;又把木杻钉住双手,那里容他些松宽。
却说施恩已有人报知此事,慌忙入城来和父亲商议。老管营道:“眼见得是张团练替蒋门神报仇,买嘱张都监,却设出这条计策陷害武松。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钱,受了人情贿赂,众人以此不由他分说。必然要害他性命。我如今寻思起来,他须不该死罪。只是买求两院押牢节级便好,可以存他性命。在外却又别作商议。”施恩道:“见今当牢节级姓康的,和孩儿最过得好。只得去求浼他如何?”老管营道:“他是为你吃官司,你不去救他,更待何时?”施恩将了一二百两银子,迳投康节级,却在牢未回。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里说知。
不多时,康节级归来,与施恩相见。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诉了一遍。康节级答道:“不瞒兄长说,此一件事皆是张都监和张团练两个同姓结义做兄弟,见今蒋门神躲在张团练家里,却央张团练买嘱这张都监,商量设出这条计来。一应上下之人都是蒋门神用贿赂。我们都接了他钱。厅上知府一力与他作主,定要结果武松性命;只当案一个叶孔目不肯,因此不敢害他。这人忠直仗义,不肯要害平人,以此,武松还不吃亏。今听施兄所说了,牢中之事尽是我自维持;如今便去宽他,今后不教他吃半点儿苦。你却快央人去,只嘱叶孔目,要求他早断出去,便可救得他性命。”
施恩取一百两银子与康节级,康节级那里肯受。再三推辞,方才收了。施恩相别出门来,迳回营里,又寻一个和叶孔目知契的人,送一百两银子与他,只求早早紧急决断。那叶孔目已知武松是个好汉,亦自有心周全他,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;只被这知府受了张都监贿赂,嘱他不要从轻;勘来武松窃取人财,又不得死罪,因此互相延挨,只要牢里谋他性命;今来又得了这一百两银子。亦知是屈陷武松,却把这文案都改得轻了,尽出豁了武松,只待限满决断。
次日,施恩安排了许多酒馔,甚是齐备,来央康节级引领,直进大牢里看视武松,见面送饭。此时武松已自得康节级看觑,将这刑禁都放宽了。施恩又取三二十两银子分俵与众小牢子,取酒食叫武松吃了。施恩附耳低言道:“这场官司明明是都监替蒋门神报仇,陷害哥哥。你且宽心,不要忧念。我已央人和叶孔目说通了,甚有周全你的好意。且待限满断决你出去,却再理会。”此时武松得宽松了,已有越狱之心;听得施恩说罢,却放了那片心。施恩在牢里安慰了武松,归到营中。
过了两日,施恩再备些酒食钱财,又央康节级引领入牢里与武松说话;相见了,将酒食管待;又分俵了些零碎银子与众人做酒钱;回归家来,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,催趱打点文书。
过得数日,施恩再备了酒肉,做了几件衣裳,再央康节级维持,相引将来牢里请众人吃酒,买求看觑武松;叫他更换了些衣服,吃了酒食。出入情熟,一连数日,施恩来了大牢里三次。却不提防被张团练家心腹人见了,回去报知。
那张团练便去对张都监说了其事。张都监却再使人送金帛来与知府,就说与此事。那知府是个赃官,接受了贿赂,便差人常常下牢里来闸看,但见闲人便拿问。
施恩得知了,那里敢再去看觑。武松却自得康节级和众牢子自照管他。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节级家里讨信,得知长短,都不在话下。
看看前后将及两月,有这当案叶孔目一力主张,知府处早晚说开就里,那知府方才知道张都监接受了蒋门神若干银子,通同张团练,设计排陷武松;自心里想道:“你倒赚了银两,教我与你害人!”因此,心都懒了,不来管看。捱到六十日限满,牢中取出武松,当厅开了枷。当案叶孔目读了招状,定拟下罪名,脊杖二十,刺配恩州牢城;原盗赃物给还本主。张都监只得着家人当官领了赃物。当厅把武松断了二十脊杖,刺了“金印”,取一面七巾半铁叶盘头枷钉了,押一纸公文,差两个健壮公人防送武松,限了时日要起身。
那两个公人领了牒文,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门便行。原来武松吃断棒之时,却得老管营使钱通了,叶孔目又看觑他,知府亦知他被陷害,不十分来打重,因此断得棒轻。武松忍着那口气,带上行枷,出得城来,两个公人监在后面。约行得一里多路,只见官道傍边酒店里钻出施恩来,看着武松道:“小弟在此专等。”
武松看施恩时,又包着头,络着手。武松问道:“我好几时不见你,如何又做恁地模样?”施恩答道:“实不相瞒哥哥说:小弟自从牢里三番相见之后,知府得知了,不时差人下来牢里点闸;那张都监又差人在牢门口左近两边巡着看;因此小弟不能够再进大牢里看望兄长,只到康节级家里讨信。半月之前,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里,只见蒋门神那厮又领着一伙军汉到来厮打。小弟被他痛打一顿,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话,却被他仍复夺了店面,依旧交还了许多家火什物。小弟在家将息未起,今日听得哥哥断配恩州,特有两件绵衣送与哥哥路上穿着,煮得两只熟鹅在此,请哥哥吃了两块去。”
施恩便邀两个公人,请他入酒肆。那两个公人那里肯进酒店里去,便发言发语道:“武松这厮,他是个贼汉!不争我们吃你的酒食,明日官府上须惹口舌。你若怕打,快走开去!”
施恩见不是话头,便取十来两银子送与他两个公人。那厮两个那里肯接,恼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。施恩讨两碗酒叫武松吃了,把一个包裹拴在武松腰里,把这两只熟鹅挂在武松行枷上。施恩附耳低言道:“包裹里有两件绵衣,一帕子散碎银子,路上好做盘缠;也有两双八搭麻鞋在里面。——只是要路上仔细提防,这两个贼男女不怀好意!”武松点头道:“不须分付,我已省得了。再着两个来也不惧他!你自回去将息。且请放心,我自有措置。”施恩拜辞了武松,哭着去了,不在话下。
武松和两个公人上路,行不到数里之上,两个公人悄悄地商议道:“不见那两个来?”武松听了,自暗暗地寻思,冷笑道:“没你娘鸟兴!那厮到来扑复老爷!”
武松右手却吃钉住在行枷上,左手却散着。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鹅来只顾自吃,也不睬那两个公人;又行了四五里路,再把这只熟鹅除来右手扯着,把左手撕来只顾自吃;行不过五里路,把这两只熟鹅都吃尽了。
约离城也有八九里多路,只见前面路边先有两个人提着朴刀,各跨口腰刀,在那里等候,见了公人监押武松到来,便帮着做一路走。武松又见这两个公人与那两个提朴刀的挤眉弄眼,打些暗号。武松早睃见,自瞧了八分尴尬;只安在肚里,却且只做不见。又走不数里多路,只见前面来到一处,济济荡荡鱼浦,四面都是野港阔河。五个人行至浦边一条阔板桥,一座牌楼上,上有牌额,写着道“飞云浦”三字。
武松见了,假意问道:“这里地名唤做甚麽去处?”两个公人应道:“你又不眼瞎,须见桥边牌额上写道‘飞云浦’!”武松站住道:“我要净手则个。”
那两个提朴刀的走近一步,却被武松叫声“下去!”一飞脚早踢中,翻筋斗踢下水去了。这一个急待转身,武松右脚早起,扑嗵地也踢下水里去。那两个公人慌了,望桥下便走。武松喝一声“那里去!”把枷只一扭,折作两半个,赶将下桥来。那两个先自惊倒了一个。武松奔上前去,望那一个走的后心上只一拳打翻,就水边捞起朴刀来,赶上去,搠上几朴刀,死在地下;却转身回来,把那个惊倒的也搠几刀。
这两个踢下水去的才挣得起,正待要走,武松追着,又砍倒一个;赶入一步,劈头揪住一个,喝道:“你这厮实说,我便饶你性命!”那人道:“小人两个是蒋门神徒弟。今被师父和张团练定计,使小人两个来相助防送公人,一处来害好汉。”武松道:“你师父蒋门神今在何处?”那人道:“小人临来时,和张团练都在张都监家里后堂鸳鸯楼上吃酒,专等小人回报。”武松道:“原来恁地!却饶你不得!”手起刀落,也把这人杀了;解下他腰刀来,拣好的带了一把;将两个尸首都撺在浦里;又怕那两个不死,提起朴刀,每人身上又搠了几刀,立在桥上看了一回,思量道:“虽然杀了这四个贼男女,不杀得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,如何出得这口恨气!”提着朴刀踌躇了半晌,一个念头,竟奔回孟州城里来。不因这番,有分教:武松杀几个贪夫,出一口怨气。定教画堂深处尸横地,红烛光中血满楼。毕竟武松再回孟州城来,怎地结束,且听下回分解。